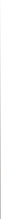顛沛流離鑄史璧
說起中國特有的傳統(tǒng)地方志��,是無論如何繞不開紹興的。因?yàn)檫@里既是我國方志之祖《越絕書》的誕生地����,又是我國方志學(xué)奠基人章學(xué)誠的故鄉(xiāng)����。
正如陳橋驛先生在《紹興市志》序言中所說:“中國有中國的方志史,紹興也有紹興的方志史���。值得紹興人自豪的是�,中國方志史是以紹興方志史開頭的��!”
《越絕書》的翔實(shí)載記����,得使我們能看到紹興昔日的輝煌。章學(xué)誠的《文史通義》�,將中國傳統(tǒng)方志理論推上了歷史的巔峰。因此有人把清代章學(xué)誠的《文史通義》與唐代劉知幾的《史通》�����,并稱為我國古代史學(xué)理論的“雙璧�����。”
從《越絕書》的誕生�,到《文史通義》的問世,用17個(gè)世紀(jì)的時(shí)間證明�,從實(shí)踐創(chuàng)新到理論成熟,是一個(gè)漫長(zhǎng)的過程�����。從劉知幾的“史通”到章學(xué)誠的“史義”����,跨越這兩個(gè)理論高峰,也足足花去了12個(gè)世紀(jì)�。章學(xué)誠的跨越,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選擇�。
《文史通義》是章學(xué)誠的代表作,它在理論上的超越前人����,并非出于偶然。章學(xué)誠生活在文化氛圍特別濃厚的紹興�,生長(zhǎng)在家學(xué)根底特別深厚的家庭里。父親章鑣是一位進(jìn)士,做過湖北應(yīng)城知縣����,對(duì)史學(xué)尤稱愛好。章學(xué)誠雖然幼小體弱多病����,卻勤學(xué)好思���。20歲以后���,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是個(gè)“史才”,大有意氣落落�,不可一世之勢(shì),更加發(fā)憤讀書��,隆冬盛夏�����,讀至午夜而不知疲倦�。盡管家境貧寒,藏書無多����,但他與其父一樣���,常以借書、抄書�、作筆記為樂事。父子倆����,一個(gè)是如饑似渴的讀書人,一個(gè)是廢寢忘食的讀書人���,所讀的又都是“史部之書”�。所不同的是�����,章學(xué)誠在浸潤于浙東史學(xué)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的同時(shí)����,更注重于分析利弊得失,總結(jié)經(jīng)驗(yàn)教訓(xùn)�,提出自己的獨(dú)立見解。從小養(yǎng)成了不可多得的思辯習(xí)慣���,為他后來的治學(xué)奠定了堅(jiān)實(shí)基礎(chǔ)����。
與同時(shí)代的其他知識(shí)分子一樣,章學(xué)誠也曾在科舉路上進(jìn)行過艱難跋涉�����。先后于23歲��、25歲�、28歲�、31歲時(shí),四次赴京應(yīng)順天鄉(xiāng)試�,皆落第而歸。對(duì)章學(xué)誠生活����、學(xué)業(yè)備加呵護(hù)的翰林院編修朱筠因此對(duì)他說:“足下于此無緣,不能學(xué)�,然亦不足學(xué)也,”勸他放棄科舉夢(mèng)想����。但章學(xué)誠深感家境貧寒,不得已而指望于此,結(jié)果是七應(yīng)鄉(xiāng)試科場(chǎng)����,累遭擯棄,直到41歲時(shí)才中進(jìn)士���。這時(shí)的章學(xué)誠�,已是不惑之年了��,本來是值得慶賀的大喜事�����。但是經(jīng)過20余年的世事磨練�,一個(gè)當(dāng)年意氣落落、不可一世的學(xué)子��,深知自己的為人和學(xué)問���,與社會(huì)潮流早已格格不入�����。所以他“不敢入仕”�,無意做官,毅然放棄為之苦苦追求幾十年而眼看就要得到的機(jī)會(huì)�,重新回到他所鐘愛的修志治史生涯。
章學(xué)誠顛沛流離�,一生坎坷,足跡遍及大江南北�����。為了謀生�,他度過了長(zhǎng)達(dá)7年的講學(xué)生活,先后主講肥鄉(xiāng)����、永豐、保定�、歸德等地書院�����。為了養(yǎng)家糊口�,他游幕安徽亳州和湖北武昌,僅在畢沅幕府中����,一呆就是五年��。此外還做過同鄉(xiāng)狀元梁國治家塾師��。然而最使他傾心的����,仍然是治史做學(xué)問����。27歲那年,他從北京回湖北省親�����,剛好父親應(yīng)天門知縣之聘��,正在主持編纂《天門縣志》�。對(duì)史學(xué)、方志學(xué)已有深入研究的章學(xué)誠���,不僅參與了縣志的編纂�����,還特地撰寫了《修志十議》��,第一次對(duì)編纂地方志提出了自己的系統(tǒng)主張����。這既是他史學(xué)天才的初試鋒芒,也是凝聚著他畢生心血的《文史通義》寫作的開始��。
此后����,他在修志領(lǐng)域一發(fā)而不可收,相繼主纂或協(xié)纂12部地方志�����。在他參與修纂的常德��、荊州����、黃州����、天門、石首�、麻城等府縣志�����,后世都有很高評(píng)價(jià)��。由他主纂的《和州志》��、《永清縣志》�����、《亳州志》�����、《湖北通志》等����,都是貫徹他方志理論的名志佳構(gòu)�。對(duì)章學(xué)誠來說,無論是修志�����、講學(xué)還是做幕僚�,甚至經(jīng)受意外打擊����,都沒有放棄他自己心愛的治學(xué)之路��。在44歲那年的求職途中���,不幸遇上了強(qiáng)盜����,所有行李被搶�,所帶44歲以前的文稿也蕩然無存!用數(shù)十年心血撰成的著作文章����,一旦被洗劫一空,對(duì)任何一位學(xué)者來說�����,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擊�。后來他雖從故舊家存錄的別本中借抄,但最多也僅存原稿的四五成���。在經(jīng)歷了這場(chǎng)浩劫之后��,每有撰述��,他必留副本����,寄請(qǐng)親友保存�,其中他的另一位同鄉(xiāng)狀元史致光抄藏文章最多。
章學(xué)誠幼小住在紹興城內(nèi)大禪法弄�,后因家庭變故,在他58歲回鄉(xiāng)后����,只好在塔山下另置房產(chǎn)。這時(shí)的他已經(jīng)兩耳重聽�,雙目失明,貧病交加���,垂垂老矣�����,可他還是念念不忘他的《文史通義》��。這部用30多年心血鑄就的史學(xué)巨璧��,可謂是撰著于顛沛流離之中��,成稿于車塵馬跡之間�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他這樣做���,既為千古史學(xué)開辟了蓁蕪���,又為后世史學(xué)立下了開山之功。
我國是個(gè)歷史大國�����,同時(shí)也是個(gè)史學(xué)大國���。數(shù)千年來��,從史學(xué)思想�����、史書編纂到史學(xué)評(píng)論等方面�,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(xué)理論。章學(xué)誠的杰出貢獻(xiàn)在于:他緊緊抓住史學(xué)靈魂�����,深刻回答了史學(xué)的根本宗旨和任務(wù)��,是總結(jié)歷史發(fā)展規(guī)律(即“明道”)和為現(xiàn)實(shí)服務(wù)(即“經(jīng)世致用”)����;他從歷史事實(shí)(“史事”)�����、歷史敘述(“史文”)出發(fā)���,對(duì)歷史理論和觀點(diǎn)(“史文”)這個(gè)歷來被史學(xué)家所忽視的重要課題�����,從根本上賦予了嶄新的內(nèi)容和意義����;對(duì)史家修養(yǎng)�����,他在前人“才、學(xué)����、識(shí)”的基礎(chǔ)上,提出了“史德”這一重要命題�,從而大大完善和豐富了古今史家修養(yǎng)的理論。
在方志學(xué)科建設(shè)方面�,他結(jié)合自身修志實(shí)踐,總結(jié)前人修志得失�,提出了一整套系統(tǒng)、完備而又深刻的方志學(xué)理論���。他以思想家特有的敏銳�,第一次提出“志屬信史”的觀點(diǎn)�����,對(duì)地方志的性質(zhì)作了科學(xué)界定���;他認(rèn)為編纂地方志的目的���,如同國史一樣是為了經(jīng)世致用��,有裨風(fēng)教���;他首創(chuàng)了以“志”為主體,以“掌故”����、“文征”為兩翼的方志分立三書體系�����;他對(duì)地方志常用的志����、紀(jì)、傳���、表��、圖�����、錄���、考以及索引等體裁的合理運(yùn)用作了深入的理論考察����;為確保方志事業(yè)世代相傳����,他還特別提出州縣設(shè)立修志機(jī)構(gòu)的主張。所有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解決����,標(biāo)志著我國方志學(xué)理論的成熟和方志學(xué)的建立。以內(nèi)容博大精深��、觀念獨(dú)特新穎�、分析透辟入理、思辯縝密嚴(yán)謹(jǐn)和充滿非凡創(chuàng)造力的《文史通義》�,自然成了我國方志學(xué)的奠基之作。梁?jiǎn)⒊虼苏J(rèn)為�,章學(xué)誠是“清代唯一之史學(xué)大師”。
可就是這位大師級(jí)人物����,他的杰出成就和重大貢獻(xiàn),由于不隨濁流和不合時(shí)好而始終沒有得到應(yīng)有重視�����,甚至長(zhǎng)期受到貶斥和誣毀。直到20世紀(jì)初����,通過梁?jiǎn)⒊⒑m等人的研究���,才逐步發(fā)現(xiàn)他在學(xué)術(shù)上的無可匹敵���,并獲得國內(nèi)外學(xué)術(shù)界的高度評(píng)價(jià)���。被法國法蘭西學(xué)院的戴密微教授稱為“是中國第一流之史學(xué)天才����?!泵绹固垢4髮W(xué)的倪德衛(wèi)教授認(rèn)為章學(xué)誠“是中國造就的最有魅力的(最迷人的)思想家之一”。
章學(xué)誠是中國的�����,也是世界的��!
(作者系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研究員���,《紹興市志》總纂����,紹興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(huì)副會(huì)長(zhǎng))
轉(zhuǎn)載來源:2010年8月11日 《紹興日?qǐng)?bào)》